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尊龙最新版
发布时间:2014-06-13
来源:古代文学教研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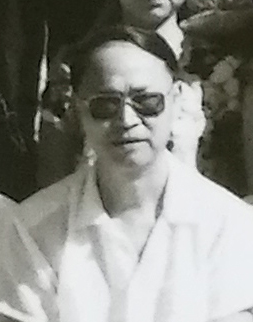
黄保真 男 (调离)
黄保真(1939—2015),山东巨野人,文艺理论家。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师从郭绍虞先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1962年本科毕业后继续在本系读研,1965年硕士毕业后留任复旦大学中文系。1967年调入《人民日报》文艺部。1979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993年举家南渡,从此任教于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并担任国学研究所所长,直至退休。退休后继续为本硕学生授课,患病后回京治疗了一年左右,不幸于2015年9月13日逝世。黄先生在古代文论领域耕耘一生,其代表作《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与蔡钟翔、成复旺合著)获首届全国高等学校科研成果一等奖。煌煌五卷本,近三百万字,黄先生主要负责隋唐五代和明清至近代部分,规模近百万言之巨。此后参与了成复旺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辞典》,又为傅璇琮主编的《中国诗学大辞典》撰写词条五十三条,等等,黄先生的研究写作未尝稍停。海南师范大学国学所近年组织人力搜检,整理出了黄先生近百万言的著论,几与“五卷本”规模相副。主编周泉根从中节选约七十万字结集出版,并借此机会为黄先生的学术成果整理叙目,既和盘托出其生平学术研究之全貌,又照鉴其为学的风范、主张和愿景。
成复旺:追忆黄保真先生|天涯·新刊
追忆黄保真先生
成复旺 2020年5月
黄保真先生去世后,他那面带笑意,不紧不慢、侃侃而谈的样子,反而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总觉得应该为他写点什么,但一时又想不好究竟应该写点什么,也不知道何处可载。前不久,海南师范大学的周泉根先生给我发来了他已经编好的两卷本、六十多万字的《黄保真先生文集》的书稿。说实话,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周泉根先生是黄保真先生晚年的学友和同事,我们曾在黄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见过一面。没想到,他对黄保真先生怀有如此厚重而实在的师友深情。他约我为此书作序,我不可能不接受。一是为周泉根先生的这种师友深情所感动;二是亦即此了结我自己的一桩心事。
黄保真先生自1979年调入人民大学,就同蔡钟祥先生和我在一起,一起上“中国文学理论史”这门课,一起写《中国文学理论史》这部书。虽然不能说朝夕相处,却的确是三天两头见面。接触中,觉得他和蔼可亲、乐于交谈、令人轻松愉悦,所以我们很快就从工作上的同事变成了人生中的朋友。其间有件事,我永远都不会忘。那时,在工资制度上中国还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层层倒挂”的年代,知识分子待遇很低。为了多少能够贴补家用,黄先生夫妇办了一家小书店。事成之后他立即来告诉我,并对我说:“以后你想买什么书,就跟我言语一声,我按照出版社批发给书店的折扣价给你带来。”我说:“你们办个书店不容易,今后的经营会很辛苦,有多少收益尚不可知;就按书上的定价带给我,就已经省了我不少事了,不要再打折扣。”这样的“讨价还价”当然不会有结果;但后来我托他买的书,他实际上还是按照折扣价算的。这件事似乎很小,但我总觉得:一个人遇到一件事,在第一时间的想法是最真实、也最珍贵的。书店甫成,黄先生首先想到的不是为自己多赚几个钱,而是给朋友多省几个钱。这几乎可以说是透明地展现了他的处世为人和内心世界。
当然,我们在一起谈得最多的还是学术。黄先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科班出身,这方面的知识原比我多,交谈中我自然受益匪浅。我也总是在出书之前先看他刚写完的书稿。他分担的清初那一章,包括顾、黄、王所谓“三大家”。这三位都是大学者、大思想家,各有丰硕的学术著作和宏大的思想体系,文学理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一般治文论者,往往以所谓“专业”的眼光,仅仅注意他们有关文学的言论;至于他们的学术造诣与哲学思想,则只从其他思想史、哲学史论著中摘取几句现成结论,在“生平简介”中敷衍一下而已。而黄保真先生不是这样,他是在考察了他们的全部著作、厘清了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之后,再由此出发去论述他们的文学理论的,故与其他同类著作面貌迥异。对于章太炎、王国维及其他许多人,他都是这样做的。可想而知,这样做要多花费多少时间、多付出多少艰辛啊!但是,认真想来:不这样做对吗?不这样做行吗?不这样做写出来的东西靠得住吗?当时有人问我“黄老师的学术有什么特点”,我回答四个字:“林茂水深。”而“林茂水深”谈何容易,那是长期潜心的学术建设和积蓄的结果。记得某年的春节期间,一位人民大学的老师告诉我们:“你们黄保真大年初二就到科学院图书馆去看书啦!”他是亲眼看见的。“林茂水深”,良有以也。
这里所说的黄先生的治学态度,与上一段所说的他的处世为人,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但我总觉得有。做人与做学问肯定是有内在联系的。在更深的层次上,它们是生长在同一条心灵之根上、是依存于同一种生命底色的。黄先生的这种心灵之根和生命底色就是:真诚。黄先生名“保真”,可谓名副其实。
黄保真先生与蔡钟祥先生,都是既有学术又有修养的人。古人云“道德、文章”。现在已经很少听到这样的话头了;但每当我想起他们,心中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这句话。因此,我们的合作才能那样美好。我曾在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新排再版的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的《再版前言》中说过:“本书的撰写方式也与众不同。它既不是一人独自承担的,也不是多人执笔、一人主编的,而是由我们三个人分工合作的。三个人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在撰写过程中,既有充分的讨论和协商,也有必要的保留和让步。但这是真正朋友间的思想与学术的交流,我们的合作是融洽而愉快的。表现在书里,就是虽然各部分保持着各人的独特风格,而全书又不失为一个连贯的整体。”这大概是学术合作的最佳状态。我们本来是打算长期合作下去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完成之后,我决定转入中国美学范畴体系的研究,并制定了计划,明确了分工,而且已经启动。但后来由于种种一言难尽的原因,黄先生远调海南,我也从中文系转入哲学系,合作计划也就大部分不了了之了。那篇《再版前言》接着说道:“当年促膝切磋、意趣融融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而如今,这一切都已经成了美好的记忆,这部书也就成了这些美好记忆的载体。”那时说这些话,还只是因为三人的分离;而十年后的“如今”再看这些话,则已经是“故人云散尽,余亦等轻尘”了。
我与黄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北京某医院的病房里。那时他已经做了肠结扎手术,不能吃,不能喝,只能靠输液维持生命。但见面时气色还好,精神也好,而且依然亲切善谈。我曾问他:“听说你退休以后还在上课?”他笑着重复说:“那是玩儿,那是玩儿。”这个“玩”字似颇可玩味。教师的职责可以届时退休;但学术活动已经化入黄先生的生命,生命不息就不会停止,也无法退休;即使那已经不是他的职责。至于一般的轻松自如、游刃有余之意,还在其次。我告诉他,我退休后搬到了郊区的农村,“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你还从来没有去过,等身体好些了,请你去看看,玩玩儿。”他说:“好哇!不知我能否闯过这一关,如果闯过了这一关,我一定去,咱们再好好聊聊天儿。”谈话间,他不时地要水;因为医嘱不能喝水,看护人员不愿给他。他无奈地跟我说:“我不是要喝水,只是口干,要点水润润口。”这时我才想到,一个不能喝水的人长时间说话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于是尽快告辞,同时反复表示,过些天再来。
不料、亦不出所料,在沉重的等待中,约一个月后,噩耗传来……
黄先生去世后,我常常想,也多次向朋友们说:黄保真是个能做学问,而且实实在在地在做学问的人。如果再假以时日,环境再好一些,会取得更多的、或许比我更大的成果。他与我,虽然在属相上有“虎”“兔”之别,其实年龄相差不到一岁。但是现在,他已经去了,而我还在。这是为什么?有什么理由吗?没有!什么理由也没有,就是两个字:侥幸。区别仅在于侥幸与不幸。那么作为一个侥幸尚存的人,对于不幸已逝的故友,除了更深的惋惜、更深的怀念、更深的敬意,还有什么?还能有什么?
成复旺,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国当代的人学与美学》等。
华枝春已满,天心月正圆
溥之
《黄保真文集》最近由海南出版社隆重推出,凡两册六卷,计七十万言,书法名家古柳刘胜角教授题签,著名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成复旺教授作序,系海南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周泉根教授带领黄先生一众弟子历时四五年编辑完成。文集精装,版式典重大方,封面幽兰渊博,一瓣心香,万顷文澜,既似牵系着先生晚岁临海之魂梦,又如先生浩瀚无涯之学问。
黄保真教授,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生于鲁西南的巨野县,洙泗之间、圣人故里。菏泽一中毕业后,于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后师从郭绍虞先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黄先生本硕连读,1965年毕业后留复旦中文系工作。1967年调入《人民日报》文艺部。1979年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993年举家南渡,执教于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并长期担任国学研究所所长。2015年9月13日病逝于北京。业师郭绍虞,文章巨擘,国学大师,书法名家,早年曾与郑振铎、茅盾、叶圣陶等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是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开创者,“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成立时第一任会长,黄先生自己也正是在古代文论领域耕耘了一辈子,其代表作《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与蔡钟翔、成复旺合著)获首届全国高等学校科研成果一等奖。煌煌“五卷本”,近三百万字,黄先生主要负责隋唐五代和明清至近代部分,规模也近百万言之巨。
两册《文集》共分六卷,收录黄先生“五卷本”之外的文章共计六十七题,既有谈中国文化特质等宏观大问题,又有品评具体作品的小文章,既有文学思想史上专精的个案研究,又有关于学术研究方法的总体看法;或是关于中国文化如国民性、道教等的点评随笔,或是经典小说、诗歌和诗文评的精彩解析,还有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分期、发展和出路的深入讨论,尤其是对古典审美范畴、文艺思想家作了独到研究,内容丰富,卷次清晰。其中如《<二十四诗品>臆解臆译》等未刊稿,尤为珍贵。编撰者在“后记”中如是评说:“本篇规模宏大,是黄先生在视力很差的情况下,逐字敲进电脑的,惜第九品未完即染恙住院。幸得黄先生的爱徒刘玥彤妥善保管,并及时出示于编者,否则必成遗珠之憾。此作体例谨严,风格独具,视野宏阔,深得文心,我辈竟不能赞一词,更无力续补。编者只能对里面的文字略作梳洗校核。‘末济终焉心缥缈,万事都从缺陷好。’有多少就收多少,总计约五万多字。“缺月挂疏桐”,亦造化之妙景。”不幸耶?幸耶?或有遗珠,却总算有七十万言整齐面世,笔者大以为“幸也”!
先生学问,视野开阔,取精用弘,诚如成复旺先生所评价的那样——“林茂水深”。先生问学,既以古为邻,又与时俱进,晚年一直关注出土文献,累积有十多万字的笔记,然其最念兹在兹、毕生耕耘的还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他对该学科知识体系的性质、特征、分期等总体性问题以及攻治这一学科的态度、视野、方法等问题,都有高屋建瓴的思考和建议。先生每每感慨当下学风之“三不通”,即古今不通、中外不通、文史不通。于中外古今之间,他非常反对在中外范畴或精神传统之间强调人的格义,特别主张回到古典生态用古典话语原其原、本其本。于文史之间,始终关注史哲话题,如“仁与勇”“天与性”“礼治秩序”“一体二用”“象数之学”“太一生水”等。于文论史,既主张回到文论话语本身,又要求跳出文论史,将文论置于文学史和文化史的背景中去考辨。
黄先生最后是从海南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这个职务上退休的,半月板老化之前,体力精神俱佳,每以宏愿示客。退休后中文系的阮忠、单正平、宋剑华和周泉根等老师先后都殷切地请其继续为本科和研究生授课,即使罹患足疾,也坚持在家讲论,五尺客厅,即三尺讲席,一直舌耕至回京看病的前半年。返京前后约一年光景,就辞别人世遽归道山。哀哉!惜哉!据我所知,学校并未正式返聘过他,刘和忠院长曾亟欲延后,奈何退休手续已办讫。先生退休后组织的诸如《道德经》《二十四诗品》等课程多非学校计划内,不仅没有课酬,还得备茶点,纯粹是个人雅好、弟子雅集,黄老师自得其乐,悠悠然不知老之将至。有好舞文者曾以世说体记之:“巨野黄公,舌耕苗圃,有仙气,乘桴浮于大海之南。退而不休,古稀之年犹设席于家,传授儒道,不图酒食之馔、束脩之供。木铎金声,优哉游哉。有就学者慨叹:‘师之所在,道之所存。风雅不坠此西席。’”
文集编竣,即有长者赋诗纪念:“耕年耜月任时秋,笑脸堪如马帐稠。崒峍书山多揽胜,窅辽学海喜遨游。李桃不识三春梦,经史偏遗五凤楼。提笔端知文品重,师心观止老黄牛。”先生文友存乎海内,可惜五凤楼中人杳然,先生弟子遍于天下,无愧粲然学海道南来。刚剞劂印行,求书电函即飞驰不绝。
可以这么说,黄保真先生最后二十年都是奉献给了天涯海角的,不少学术成果是在海岛上取得的,很多美好的学术愿景、宏大的学术规划也都是在海风中设想设计的。《文集》能叙录其学术成果、整理其未刊之作,甚至转达其晚年之学术心声、愿景,诚功莫大焉!海南出版社组织优秀队伍编校出版是集,让大海之滨继续传布着邹鲁之邦的木铎金声,亦善莫大焉!笔者注意到,海南社最近奉献了不少好书,如李勃先生的三卷本《海南编年史》,其与《黄保真文集》一道,皆可谓学林之美芹、出版之佳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