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尊龙最新版
发布时间:2016-02-22
来源:罗兰·博尔
提笔准备写这篇小文时,还在正月。此时的我离开人大、离开北京已将近八个月。离开的方式很特殊,不是交换,不是读研,而是转学。这个决定的背后有太多缘由,却恰如当时发给楠神的短信中说的那般:“当初转专业,如今转学,始终在这条路上,渴望走得更远。”于是,就这么一路走到了多伦多,双修东亚研究和媒体研究。也正是在离开之后我才渐渐发觉,在文学院积累的点点滴滴是如何绽放成异乡寒窗外的星光,照我书案,引我前行。这其中就包括roland boer教授带给我的启迪。
当时本是抱着出国前练一下英语的目的报了roland boer教授的校选课popularcultureandreligion,没想到这门课带给我的收获远不止于听说读写的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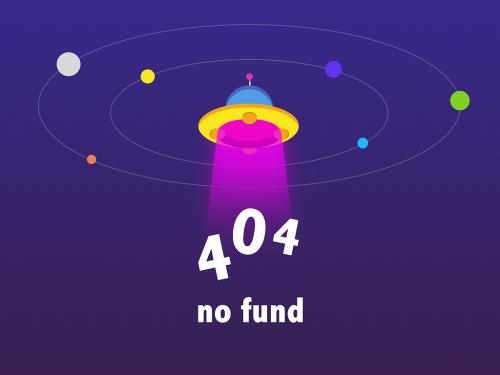
传统的中式课堂中,老师传道授业,重在“传”与“授”——老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坐在底下听。在为人师表的传统义务“传”与“授”方面,roland分毫不差。然而比大多数课堂单向“输入(input)”多的是,你会发现自己在roland的“启发(inspiration)”中不知不觉地“输出(output)”。而在这个过程里,有些不曾思考过的问题,或者曾经得不到答案的问题,似乎在与他一同的“探索(exploration)”中渐渐得到解答。
宗教曾经怎样统治世界,今天我们是否还被它潜移默化地影响?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有何异同,它们是如何塑造了中西差异?《阿凡达》里的大地之母,《指环王》里的罪与赎,《低俗小说》里的圣经,《黑客帝国》里真实与虚构的颠覆……在不到十个人的教三课堂里,在大书房咖啡厅里,roland和我们“聊”了一个学期。我们从来都把他当朋友,他似乎也没有刻意将我们当学生。平日里他聊起自己的感情观,我们听着也忍不住发表一点看法。
我仍记得他是如何认真倾听我用不流利的英语表达自己的观点,如何报以微笑、肯定与评价;我记得他渊博的学识,幽默的谈吐和发光的脑门儿,从上帝到马克思,无一不通、无一不晓;我尤其记得他在黑板上歪歪扭扭的写下自己的中文名字——“薄国强”,然后一脸呆萌地说“theysaidthisnameperfectlyfitspeopleatmy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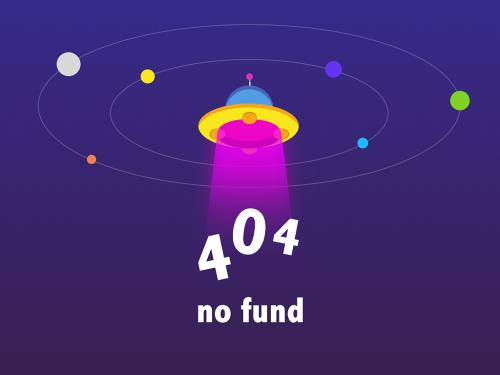
引用当初助教米兰姐的“警告”——“如果你以为这是门水课,看看电影就能得3.7,那你就选错了。”那么这样一门需要阅读、思考与参与的课程,它探讨的问题有什么用呢?humanities有什么用呢?也许就是没用吧,它们看不见也摸不着。而正是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塑造了我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填充了我们的思想、精神与灵魂,使人之所以为人;正是它们奠基了人类历史上一次次惊天动地的大改革,吸引着每一个时代的学人求索其中,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而当问起在频繁讨论政治经济的今天为何还要学习人文科学,roland这会儿眯起眼睛笑开,说:“learninghumanitiesisawayforhumanbeingstogettoknowmoreaboutthemselves.”这又怎么可以轻轻松松的以“用处”两个字来形容?
来时行囊里唯一的一本书是《西方文论概览》,脑子里装的是先秦到当代的文史,啃书本的功夫来自当初文院老师们的“压迫”。当曾经相识的概念变成英文出现在课堂上的时候,倏然想起耿老师永远不抬眼皮的“灵魂的眼睛”,想起杨老师彼时听来颇为“迷幻”的阐释,想起曾经不喜欢或听不懂的种种,种种……恰是这些,让我幸存于每周上百页的reading,让我的作文从未低于80分,让我在“歪果仁”主导的课堂讨论里没有沦为沉默的大多数。
耿老师曾告诉我们,文学院的英译“school ofliberalarts”缘出于中世纪大学的自由七艺(liberalarts)——是希冀,亦是嘱托。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都不该视为负担,而是自由与美的流溢。想到《会饮篇》里自己最爱的一句“如果世界上有任何值得为之生存的东西,那便是观照美”,纵是加国的冬夜寒冷漫长,柏拉图与我同在。读书人,不孤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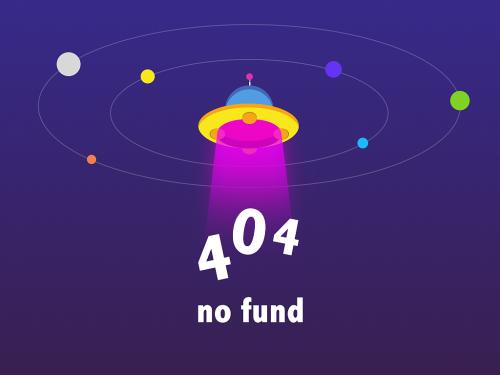
文学院2012级本科生
李丹璐
2016年2月11日,于多伦多
课程名称:大众文化与宗教(popularcultureandreligion)
任课教师:薄国强(rolandboer)
上课时间:每周一18:00-19:30
上课地点:公共教学二楼2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