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尊龙最新版
发布时间:2018-10-25
来源:
2018年10月23日,应我院邀请,中国神学研究院(香港)助理教授、道风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洪亮博士在人文楼二层会议室举办了一场题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德语世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读类型”的主题讲座。讲座由我院梁坤教授主持。
洪亮博士将那一特定时段德国学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术史置于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详细介绍了最早的自然主义解读和自然主义裂解之后的三个主要面向:凡登布鲁克的种族问题、施密特的政治神学(神话学)和巴特的辩证神学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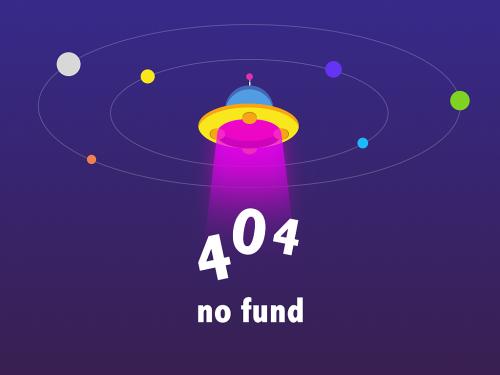
从德语世界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状况可见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其作品中的自然主义维度。最早出现的是《穷人》节译本(1846/1847)和《死屋手记》节译本(1863),直到《拉斯科涅尼科夫(罪与罚)》(1882)被翻译出来之后,作家才受到德语学界的充分重视。其大部分作品在1882-1890年间被译为德文。他们分析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客观描绘、对心理活动的精确再现以及其中蕴涵的同理心和人道主义。
洪亮博士尤其关注德语世界问世于1906-1919年的首套《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所具有的重大转折性意义。这套德语译本消解了传统德语斯拉夫学界赋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然主义”色彩,为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语文化圈构造出一个无法归类、内涵复杂的思想形象,使当时的斯拉夫学界逐渐失去对这位俄国作家的诠释主导权,转而让位于德语文化理论界、哲学界、神学界以及政治理论界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诠释。其作品中反映的种族问题、人性问题、宗教问题这三个维度转而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而这些文化理论、哲学、神学及政治理论的“非斯拉夫”研究视角带有鲜明的现实关怀,目的在于借陀思妥耶夫斯基反思自己身处的现实世界。

首部德语《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的策划者之一凡登布鲁克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找到了自己“东方意识形态”(反城市化、反民主)的代言人,并为《全集》撰写了15篇前言及导论。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暗含种族主义思想,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虽不是革命家,却关注“一种内在的、精神性的灵魂革命”,并构想了“一个理想的、神秘且充满灵性”的俄罗斯民族,通过“表达了俄国式的疯狂和俄罗斯的悲剧”,为现代俄国创造了“神话”,使俄罗斯现代民族文学的发展有了基础。但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罗斯民族的认可其实是对日耳曼民族的认可,比如,他主张斯拉夫民族未来需返归君士坦丁堡和印度,而不是向西伯利亚和东海地区扩张,这其实暗指远东地区需留给日耳曼民族扩张势力。
施密特从政治神话学角度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并称其为“泛斯拉夫诗人和先知”。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存在着矛盾的心态,一方面认为他是敌视西欧文化与天主教的俄国“野蛮”族群代表,另一方面又肯定他对天主教内在的权力属性有深刻认识。施密特认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大法官”形象,认为这体现了罗马教会的使命。他将“宗教大法官”与霍布斯的契约理论相结合,对上帝“全能”概念进行偷换,主张该概念对应利维坦所代表的权威本身的全能。洪亮博士指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上帝的全能其实是破碎的全能,而非绝对权力意义上的全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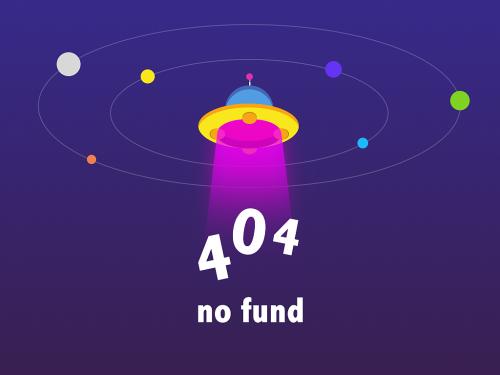
最后,洪亮博士介绍了辩证神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在巴特(karl barth)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聚拢了19世纪末已然四分五裂的欧洲灵魂,其存在超越了民族性。他指出其作品中选择的地点往往是城市的边缘化地带,如小巷、妓院、监狱等。此外,巴特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患有癫痫,能够体验到死亡的绝对瞬间的迫近,而观察其笔下的人物似乎也大多“有病”。这种病最终指向上帝,指向无从索解的生命疑问,但人物最终在因终极问题而罹患的疾病中辨认出生命的意义。
洪亮博士用鲁迅在《<穷人>小引》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为结语,指出其评价同当时德国学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具有紧密的联系。他指出,虽然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斯拉夫派重新收复失地,并宣称这些“外行”的解读为自说自话,但以上这些“外行”学者的解读同一战前后的历史语境紧密相连。通过分析这段奇特的接受史,我们能够看到当时德语学界所处的驳杂现实,而这些观点也与当下欧洲的“新右翼”思想形成了一定的承接作用。

文/张驰
图/孙诗淇 余恬
编辑/久胜